阿贝尔·加缪在法国知识与文化生活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加缪热的持续流行是什么原因?他的流行又有怎样的影响?《雅各宾》杂志的丹尼尔·芬恩(下面简称DF)与北卡罗莱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的法国与法语文学研究助理教授奥利佛·葛洛格(下面简称OG)讨论了这一问题,他是《加缪导读》的作者。
东风:
加缪在当代法国文化生活中的位置究竟是怎么样的?
和
这是一个很难概括而论的问题。加缪在法国文化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你可以在当地书店里找到一整个书架的加缪通讯或是有关加缪的书。加缪也出现在剧院里——我记得最近就有一场与他有关的歌剧——他也出现在电影里。一位朋友对我说,现在巴黎上演的某场独角戏中甚至直接朗诵加缪的日记。
同时,加缪可能是最常被政治家引用的法国小说家/哲学家。他被所有人引用:从安那其小兄弟会到极右翼,还包括现任总统埃曼努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2009年甚至有一场让加缪进入万神殿的运动——法国的“大人物”全在里面。
当然还有漫画,还有阴谋论,我想加缪是真的无处不在——杂志封面上处处有他,从左翼到右翼。在法国当代文化景观中,他是个很难回避的人物。
DF
从写作背景与写作方法上来说,是什么让加缪与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区分开来?
和
首先一点,加缪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以东大约100英里。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清楚,然而更有趣的——同时也是让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有趣作家的——是他的社会背景。
加缪同时和以前的大多数法国作家都有资产阶级背景,但加缪来自非常朴素的家庭。他母亲是女佣。他父亲在加缪出生后大约一年就去世了,当时正要去管理一个酒庄。加缪成长在公立学校体系中(在法国就是那些不用花钱就能上的学校),他不得不在上学的同时工作。高中时他每年夏天都在一家商店工作,到了大学也要打工。
他第一部出版的小说就与此有关——主角是一个办公室白领。他从出身贫苦者的角度来写作,这是他与诸如萨特、马尔罗、格诺、纪德等在加缪出道时就在他身边的人物之间最大的不同。
DF
关于二战之前,加缪青年时代在阿尔及利亚时的政治面貌有什么线索吗?
和
加缪早年参加了呼吁改革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运动。一方面,加缪在法国免费教育制度中成长起来,历史书上美化法国历史以及法兰西共和国的开化事业。与此同时,加缪注意到阿尔及利亚的日常生活中的种族隔离的状态,而他试图将这两种状态调和起来。
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前总督维奥利特提出了一项妥协法案,授予大约五千名阿尔及利亚人公民权。在这里的阿尔及利亚人是在指法国1830年入侵阿尔及利亚前就生活在那里的阿拉伯人和卡拜尔人。
这一法案是非常温和的妥协尝试——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创造一个顺从法国殖民共和国的精英群体。加缪支持这一法案,想要法案获得通过。他写作或者说参与写作了支持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宣言。在他战争之前的青年时代,他最开始的形象是殖民制度改革的支持者。
DF
加缪1935年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两年后又离开。为什么他加入之后又选择离开?对于同时代的争议话题,如西班牙内战和莫斯科大审判,他是否有过公开的表态?
和
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取决于你阅读的是哪一部自传,在加缪加入法共的问题上又是听从谁的意见。对他为何离开——或是被开开除的原因不甚明晰。可以确定的是,1935年他大学时代和高中最后一年的导师让·格勒尼耶(Jean Grenier)鼓励他加入法共。
加缪肖像,New York World-Telegram and Sun Photograph Collection,1957. Wikimedia Commons
他们有信件往来,然而通过往来信件,可以确定的是加缪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记得他在某处说过他永远不会将马克思的《资本论》放在一个人和他对生活的享受之间。同时,在青年加缪那里,他也谈到了阶级斗争是多么虚幻。
然而问题仍然很多。为什么他加入了共产党?那时,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正在经历政治路线上从头到尾的转向。党从将反殖民主义为重要路线的列宁主义转向别处。共产党说:“让我们来彻底改变社会关系吧!但是要在帝国内部。”
加缪就是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人们说他加入共产党的目的就是影响其中的阿拉伯人,但没人说过他应该做些什么。1937年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未能获得通过对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加缪就是在那时离开的。那时候许多阿拉伯激进分子也离开了共产党组建了他们自己的党。
有观点认为,加缪加入共产党为党工作时,他试图阻止阿拉伯人和卡拜尔人激进分子分离出去创建自己的党。当他发现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他就没有理由留在党内了。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下,1930年代中期的共产党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事实上,共产党内有着生机勃勃的文化生活。当时有一个叫做“工人剧院(Théâtre du Travail)”的剧场,加缪退党之前参与了不少工人剧院的工作。这也为他提供了一个与其他知识分子交流的渠道。加缪与其他人合写了一部戏剧,有时自己也登台表演,对他来说是另一种吸引。但加缪从来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共产主义者。
DF
加缪在1940年开始的德国占领中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他是怎样参与到抵抗运动中的,参与得有多深?
和
我们需要向后追溯一些,回到1940年以前,回到战间期,那时加缪正在被法国政府所拒绝。他拿到了学位,但法国政府说因为他有肺结核,他们不想让他在公立教育系统工作。他没有工作也没有前途,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想象一下你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没人愿意雇你——尽管这种事现在经常发生。
加缪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与帕斯卡·皮亚(Pascal Pia)一起在《阿尔及利亚共和报(Alger Republicain)》工作。他最开始是记者,很快就成了一位编辑。在他的编辑生涯中他采取了非常反战、拥护和平的立场,甚至到了法国政府对这份报纸进行审查的地步。加缪是个和平主义者,这毫无疑问。他反对战争,一点也不想参与到战争中去。
报纸被夹了,但加缪还得活着,所以他从阿尔及利亚搬到了巴黎,为《巴黎晚报(Paris-Soir)》工作。他恨透这份报纸了,这是份不入流的小报。过了很久他才加入到抵抗运动中。当他的报纸被关掉之后,他回到了奥兰,随后又搬回法国。
因为他的肺结核,医生建议他去南法里昂与圣埃蒂安附近的山上休养,而他的朋友们都参与到了抵抗运动中: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以及帕斯卡·皮亚(Pascal Pia)。加缪什么时候加入到抵抗运动中仍然不甚明晰。我的意思是,假如你读了二三十年前出版的自传和文献,里面会说他是1942年加入的,但是他实际上1943年12月或者是1944年1月加入的,这件事没法确定。
加缪是怎么加入的,又做了些什么?他没当过交通员,也没拎着冲锋枪上过前线。他写过一些信件,叫做“给一位德国朋友的信”,加缪在这些信中基本上就是阐述了法国加入抵抗运动与纳粹斗争的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花了那么久才加入抵抗运动中。他谈到了自己是如何想要躲开历史又怎么卷入其中,加缪对于德国人将他拖进历史中的行为十分厌恶。
除此之外他做了什么?1942年他出版了《西西弗斯神话》,其中一部分是关于卡夫卡的,当然这部分没能通过审查。占领时期法国所有的文学出版物都要受到审查。有一份“奥托名单(list Otto)”——奥托·贝兹(Otto Betz)是负责监视法国文化生活的德国官员,所有犹太人作家都被禁止了。
因此,加缪将他关于卡夫卡的章节替换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章在1944年春天单独出版。在这之后他出版了两三封致德国友人的书信。他应该在1944年参与了一份叫做《战斗(Combat)》的抵抗运动刊物的社论写作。他的戏剧《隔阂(Le Malentendu)》是他在巴黎占领期间的发表的最后几部戏剧之一,就在8月巴黎解放之前。
总的来说,他当时算是一位社论家。他写了一些戏剧,为一些报刊出过力,参与到了一份当时规模颇大的地下刊物《战斗》报的出版工作中。但这都是后期的事了,而且当今法国没有人读过这些出版物后会认为这是他对抵抗运动的介入——或者说他确实介入了,只不过从来没有被清楚地讲述过。
DF
加缪最初是怎样和让-保罗·萨特联系上的?
和
最初他们是间接地联系的。加缪评论了萨特的大作《恶心(Nausea)》。他在1930年代的地下出版物中发表评论,而他并没有多喜欢《恶心》。我的意思是,他喜欢这本小说,但是他不喜欢作为哲学理论的注释的小说。他说他希望萨特的新作不那么哲学,更像纯粹的小说。
1942年,萨特评论了《局外人(The Stranger)》与《西西弗斯神话》。有趣的是,他觉得这是对哲学的绝佳注解。同时,他解释——也带着一点责备说,加缪不懂他所引用的哲学家。这一评价堪称正面,但同时又采取了一种非常专业的语调。加缪给格勒尼耶的信中提到了这一评论说:“他的口气颇为刻薄,但他确实理解了我的作品中我未曾理解的部分。”
所以他们的交往最开始有些矛盾。崇拜中又有不少的厌恶,不管是萨特还是加缪,也许双方都差不多——这就说不清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1943年6月,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萨特戏剧《苍蝇(The Flies)》的开场。他们的初次见面之后就很快熟络起来,经常互相走动。
DF
战后法国左翼知识界,包括像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这样的大人物对法国共产党的态度以及苏联的态度是什么?加缪与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和
二战之后的苏联在法国享有盛誉,他们把纳粹揍趴下了——然而这些被当代法国人遗忘了。斯大林格勒是态度的转折点。许多人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后加入了抵抗运动。苏联是欧洲的解放者,这是当时的共识。
当然,法共也在这场胜利中分了一杯羹。法共是最先参加组织的党,他们管自己叫“战斗党(le parti des fusilles)”,意思是说他们是所有政党中有最多杀纳粹的激进分子的党。在当时的法国,只从人数上来看,法共是最大的党:我记得他们有议会中四分之一的席位,26%的选民,他们的声望极高。
他们有自己的出版物。不只有《人道报(L’humanite)》,还有《法国文学(Les Lettres Francaises)》。当时的法共党员都有谁?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名字,从毕加索(Pablo Picasso)到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都是法共成员。他们影响力极大,名望极高,一般人的态度就是崇拜和敬佩。
尽管萨特和波伏娃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党员——萨特转向了第三条道路——但他们确实明白法共在工人阶级中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
波伏娃和萨特在北京,1955 刘东鳌摄,新华社
战后最初的几年,加缪仍然不愿直接批评法共,因为它是抵抗运动大家庭中的一部分。但不久之后他就开始迅速在反殖民战争上与法共分道扬镳。那时印度支那人民正在与法国殖民系统斗争,亨利·马丁(Henri Martin),法共领导下的CGT成员,因此被法国政府投入监狱。萨特对反殖民斗争介入很深,而加缪则并未介入其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代表了大写的历史,它代表了人民的进步解放事业——或是激进的、直接的解放事业。它代表了对纳粹主义的抵抗,你可以顺从它也可以抵抗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选择,而加缪拒绝选择。他不想被逼迫着选择阵营,这立刻就让他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不和。所以,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战后期与他们并不亲近。
当然,在法共这个议题上,萨特与波伏娃也可以分为不同时期。他们最终在1952年左右与法共亲近了。重要的是,加缪从始至终都不是法共或是苏联的朋友。
他总是对殖民地独立运动保持警惕,因为它们背后是苏联的支持。所以他很快将苏联视为威胁。萨特也会谴责苏联,但是仅限各种特殊事件,如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或是1968年9月布拉格之春。加缪总是反对苏联,而萨特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谴责它。
DF
我们之前谈到了政治行动主义以及加缪的政治立场。然而他今日最出名的作品无疑是小说。从他的小说中说出的或是没说出的东西来看,能发现加缪怎样的政治面貌?
和
这就需要讲到加缪作为定居者(colon)的身份了。在法语中,他们叫做“pied-noirs”,意思是“黑脚”。他被那种在公立学校中那种慷慨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观念撕裂了。那些教导他的老师来到他家中,教授他知识,将他从自己的社会阶级中提升出来,帮助他成为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当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之后,他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和补助,以及奖学金。他在法国认同和阿尔及利亚认同中被撕裂了,而他关于法国的第一手知识就是,它是一个殖民的、压迫的国家。
最初,他试着在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及其失败中,以战斗姿态修复这种裂痕。随后他做了一些关于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的山地地区——山民艰苦生活的报告,而这同样以失败告终。所以,他写作《局外人》——他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最出名的一部——时,他开始放弃了。他小说中的角色,那些从不说话的人,那些没有名字的人,全是阿拉伯人或卡拜尔人。所有其他角色,那些来自欧洲的白人都有话说,他们作为人类而存在。
对于21世纪的读者来说这一情况是令人震惊的。但在当时,这是殖民秩序中的真实状况。他完成了对这种现实的再生产,虽然没有明说。
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对殖民现实的拒认——对作为人类的阿拉伯人和卡拜尔人的拒认。我们有像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这样的十九世纪作家谈到这些问题,然而在这里加缪将它们统统擦除掉了。人们花了很久才意识到小说中的这一面向:“等一等,这小说敢情是讲这个!”大家都以为它是挑战天主教和向上爬的社会习俗。然而,与此同时它完全没有质问殖民主义与它的不公。
1970年,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写了一本关于加缪的小书,指出了这一点。1970年代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是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与亨利·克雷阿(Henri Krea),他们早些时候写了关于加缪与《局外人》的文章。总的来说,要等到萨义德这样的批判才开始出现,而时至今日在法国仍没有什么影响力。
1947年写作的《鼠疫(The Plague)》——一部因为新冠病毒在现下十分流行的小说——被广泛地视为德国占领时期的寓言。在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奥兰,疫病发生了,启蒙的精英男性——医生和诗人——用尽全力逆境对抗。今天每个月都有关于《鼠疫》的评论文章冒出来,关于它是如何讲述了一个人类同压迫与逆境斗争的故事。
加缪的定居者身份从他的小说,从作品的身体中逐渐显露,《鼠疫》就位于这一进程的中点。假如说《局外人》是种拒认的话,那么《鼠疫》就是被压抑物的回归。可以将鼠疫视为一种对阿拉伯人与卡拜尔人叛乱的恐惧,一种对历史运动的恐惧。
从1830年到1947年,叛乱和抵抗从未停止。法国在阿卜杜·阿拉-卡德尔(Abd Al-Kader)那里遭到了巨大的军事失败。1870年有卡拜尔人叛乱。零星的叛乱在整个地区时有发生,对人民——人民中的绝对多数——的恐惧一直持续着,这片土地上百分之九十都是阿尔及利亚人,而不是法国定居者。对于加缪这样在法国公立教育系统中受教育的人,而这种教育几乎全是关于法国农民和资产阶级是怎样蜂起反对贵族制的。阅读法国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这种从中世纪到法国大革命的缓慢进展。
《鼠疫》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缓慢发展的体现。在法国殖民地不可避免的灭亡中,有一种对这一运动的恐惧,对法国殖民压迫的抵抗最终会获得胜利的恐惧。
在《鼠疫》的最后,是对疫情结束的庆祝。然而小说的主角,也就是医生说到,好吧,现在能平静几年了,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再次回来,那时定居者们会死去。这是他对未来的预言。当然这不是加缪认同的解读,但你肯定可以这样去阅读《鼠疫》,这就是定居者们隐秘的恐惧。
第三步——对加缪未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第一个人》一种解读方式。这是一部几乎不加掩饰的自传小说,是对他定居者身份终结的一种哀悼。
一个定居者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称自己为“第一个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前人的拒认。由于是手稿,加缪有时会将主人公称为亚当。这部小说是对定居者的辩护,加缪将他们称为阿尔及利亚的“土著”。
可以将《第一个人》视为加缪对定居者身份最终的承认。在小说的最后是忏悔。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叙事进程。有趣的是,《第一个人》在他死前一直未出版。读者必须等待这部小说重见天日,这是加缪本人的决定。
DF
加缪对于法国在1945年以后发动的殖民战争采取了何种态度?他在私底下和公开场合是怎样表达这种观点的?
和
加缪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意见总是含混不清的。1945年5月8日,在欧洲胜利日那天,阿尔及利亚人决定游行示威支持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在内的诸多事务。示威者主要是由阿尔及利亚二战老兵组成的。
他们刚刚从前线返回家乡,参与了意大利战场的法军胜利,在1944年初,戴高乐向他们许诺,只要他们与法军一同战斗,就能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人为法国人战斗,可他们却没有投票权,这是殖民制度中主要的不平等之一。
示威在1945年5月开始。法国警察撕碎了他们的旗帜和标语,一场暴乱发生了。死了一些警官,而法国政府的回应是整整两周的飞机大炮轰炸。死亡人数有数万人——数万阿尔及利亚人死去了。而法国媒体根本就不谈这件事。
幸运的是,加缪当时写了不少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章。他认为警察和军队的行为很合理,用“展示力量”一词来描述他们的行为。与此同时,当他提到示威者时——定居者和警察大约有100人左右的伤亡——他就管他们的行为叫“大屠杀”。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出他是殖民司法的支持者了。他想说,我们要和平,而不支持任意一方。可他却把一种形式的暴力称为“力量”,对被殖民者的反-暴力(counter-violence)却称为“暴力”或是“屠杀”,他站哪一边就再清楚不过了。
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叫做“不是受害者,也不是迫害者”。两年后,法国政府杀死了数以万计奋起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马达加斯加人。加缪又一次带上有色眼镜,将马达加斯加数万人的死与几个定居者之间等同起来。即使是他公开的写作和见解就已经很成问题了。
私底下加缪的问题就更大了。例如,1954年印度支那人民赢得了奠边府的胜利——就像印第安人战胜卡斯特(Custer’s Last Stand)那样的伟大胜利,最终获得了独立。加缪对法国在奠边府的失败的感情和法国沦于纳粹手中的失败的感情是相同的。这里暗含了一种纳粹与印度支那的对比,而其他人比如萨特会说他们之间完全不同。他很大程度上站在了殖民者那边。
DF
他与萨特分道扬镳是为什么?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在哪里?
和
加缪与萨特早有嫌隙——即使在1945年以前,他们之间就已经有不和了。那时,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当代(Les Temp Modernes)》杂志的编辑之一,写了一本支持苏联的书。加缪和他大吵一架。梅洛-庞蒂跟他说:“你要么跟苏联站在历史的一边,要么反对它,没有第三种选择。”加缪和梅洛-庞蒂因为这事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和萨特也一样。
但是加缪与萨特真正分道扬镳要到1951年加缪写作《反抗者(The Rebel)》。加缪写作的时间要早一点,但它是在1951年发表的。萨特的当代出版社的人很尴尬,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他们写了篇评论。
我们先回溯一下。加缪在40年代早期的理论是荒诞理论,世界是荒诞的而且没有任何意义,这是第一种荒诞。对加缪来说有两种荒诞,第二种荒诞是对第一种荒诞的实现,所以你就不得不像个荒诞的男人那样生活——我说“男人”是因为,加缪宇宙里根本没有荒诞的女人。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不会作为有智慧的存在出现。
这是非常虚无主义的观点。随着二战与纳粹主义的壮大,加缪修正了他的观点。他同样修正了他当时正在写作的一部戏剧。他当时正在写作《卡里古拉(Caligula)》,这部戏剧被他修改了。他加入了对反抗的见解,试图将荒诞中注入伦理学的面向。然而《反抗者》实际上是在谈论反叛不应是什么:它不应该是革命。反叛应该是自发的,不能是精心策划的,它不能是一个系统,也不能有计划。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反叛不能是共产主义的,它在本质上反对共产主义。
他同样反对反殖民主义运动,因为在加缪那里,反抗的首要原则就是,它不能发生在欧洲之外。这不仅仅是将纳粹与苏联并置的问题——在那个时代这算得上是惊世之论。他把反抗和反叛限制在欧洲国家之内。
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哲学家、《当代》杂志的作者之一,在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中为民族主义者一方工作,负责写作《反叛者》的评论。这篇评论颇为严厉,认为加缪过于关注苏联的越界与罪恶:古拉格、入侵芬兰波兰等等,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和塞内加尔等殖民地的罪行却熟视无睹。
加缪直接在《当代》杂志上对萨特做出回应。他主要攻击萨特,完全没把让松放在眼里。他对让松和萨特下了最后通牒:“我不会对此做出回应,也不会考虑你们提出的任何条件,直到你们做出让步,彻底地、永久地声讨苏联的罪行。只有这样我才会考虑其他问题。”
这还没完。萨特以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做出回应,事情演变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他对自己被拖进这场争论中感到遗憾,现在所有人都会为了这场公开的口水仗把他们当作笑柄了。
他拿出了老一套,谴责加缪在1942年的写作缺乏知识严谨性。接着,他又指责加缪不读原始文献,几乎像公开处刑一样。然后他又在殖民主义罪行和法国干预政策上揭加缪的短。开弓没有回头箭。萨特也指出自己曾经多次声讨过苏联。
这件事的后果就是,不管站在萨特那边还是站在加缪那边,所有人都同意加缪被狠狠羞辱了一通,萨特和让森占了上风。最后,这场争论究竟吵了些什么?我想是关于反马克思主义(anti-Marxism)与殖民主义的问题。萨特想谈的是人道主义,最后却扒了加缪的皮。在那时,加缪彻底丢掉了他的信誉。几乎没人来为加缪辩护。我记得他应该是搬出巴黎避了阵风头。他写了关于这次决裂的小故事,随后又为这件事写了一部小说。
他们决裂之后就再也没说过话,之后就是加缪去世了。那次决裂他们掐的最狠。在加缪的每部短篇集、每部小说中都在攻击萨特。萨特即使是在加缪死后也在一直贬损他。
悖论在于他们决裂了,但他们却因此而不可分割。这一决裂的影响改头换面之后仍然存在于今日法国的政治与文化气候中。
DF
加缪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和
在我们这里,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是它开始自1954年11月,因为这是宣战的日子。法国士兵涌入阿尔及利亚,然而这不过是浩如烟海的事件中的一个而已。尽管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the FLN)在那时发表了宣战声明,但没人意识到这是战争的开始。
所以加缪其实也没说什么。我记得11月他正在罗马度假,最后,很明显有些事在发生,有不少人敦促他站出来表态,但他一句话也不说,直到1955年初。他的立场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但他想说的不过就是,法国统治是福报,法国确实不够公平也不够公正,但你们阿尔及利亚人闹独立可就太不懂感恩了。
随着战事推进,他的立场也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呼吁民事休战。他想要所有派别——民族解放阵线、阿尔及利亚国民运动(the MNA, Algerian National Movement)以及法军——停止对平民的攻击。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从1830年开始,针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从来就未曾停止过,民族解放阵线造成的伤害和法军在漫长的历史上造成的伤害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
加缪在1955年1月前往阿尔及尔,发表了呼吁妥协的演讲。定居者根本不想听他说了什么,他们想要的是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全面支持,任何妥协都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事实上,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定居者中的一部分不仅不想要阿尔及利亚,甚至连法国都不想要,他们将美国视为榜样。这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愿望,最终在法国引起了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
加缪在阿尔及尔得到的只有定居者们——他的自己人——无尽的嘘声和咒骂,他们喊着“加缪去死”。而会议的组织者出乎加缪的意料,全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可以说加缪在这里就是个工具人,目的就是为了塑造定居者们冥顽不灵的形象,他回到巴黎时非常憔悴,拒绝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这件事。
他确实重发了几篇写阿拉伯人和卡拜尔人生存状况的文章。他在30年代写过一系列文章要求法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救助,又在这时重新出版以展示他的诚意。他选择了几篇文章,有几篇过于家长派头的文章没有收录。
他还试着对部长们施以影响——当时的司法部长是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and)——为民族解放阵线被判处死刑的激进分子争取减刑。他真的非常努力地在促进妥协的达成,然而归根结底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是反对独立的,因为他坚持要达成妥协。他会说些“殖民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一类的话,但他想要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
他的计划之一就是提议阿尔及利亚拥有自己的旗帜,除了军事和经济事务什么都自己说了算。听起来很熟悉是不是?今天大多数西非国家都是这样的。它们名义上独立,但是它们的货币——现在是Eco,以前是西非法郎(Franc CFA)——是由法国国家银行(French National Bank)所控制的,到处都是法国军事基地,而这正是法农警告我们的。
加缪的妥协方案没有改变法国控制前殖民地国家财富的事实。不用说也可以想象得出,阿尔及利亚人对这些妥协一点也不感冒。
DF
加缪的名声在他去世时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间是什么样的?对加缪的重估展示出的法国政治与知识界的转变是什么样的?
和
加缪在1960年1月去世,而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从1954年一直持续到1962年——这一点很关键。在法国大都市中的人们已经为这场战争精疲力尽,而加缪的立场被视为殖民主义倾向。同时,加缪也被他同萨特的决裂拖了后腿,而萨特当时正如日中天。萨特起草了一系列针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与法国政府实施的酷刑的宣言,而加缪则保持沉默。
当然,他的名声也为他带来了不少抗议与情绪的宣泄。在他的车祸发生地附近,他们发现了一份手稿。我记得安德烈·马尔罗说:“把它带到伽利玛*去。”那份手稿就是《第一个人》。
*伽利玛,应是指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1911年创办的出版社,法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对20世纪法国文学有重大影响。
加缪的妻子与密友读过手稿后认为现在不是出版这样一部维护阿尔及利亚法国定居者的手稿的时候。这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已近尾声,而一旦战争结束就没有哪个法国人读这些破事了。这件事完全没上新闻。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没人对殖民主义怀有乡愁,这时候出版《最初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当然,这也是五月风暴的时代。法国上下洋溢着革命造反的氛围,知识分子各个都是共产党员,而像加缪这样的人因为某些特殊理由在1935-1937年的短暂时期之后就退出了。这不是加缪的时代。
我认为对加缪的重估要在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开始。68年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但随后发生的反革命却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们回过头来发现共产党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而纷纷脱党。一些人加入了毛主义党,但更多人转向了右翼——那些人曾在《当代》杂志上发表文章,和萨特一同工作。法国的知识生活大大改变了,远离激进的社会改变,转而拥抱新自由主义,在这一转向背后是反共主义的社会环境。
反共先锋来来去去,法国电视台可喜欢他们了。这帮人声势越来越大——像安德烈·格鲁克曼(André Glucksmann)和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 Henri-Levy)。叫他们知识分子就是抬举他们,可他们确实是各个都上了电视,天天嗡嗡个不停。这为加缪的“归来(意味深)”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1989年柏林墙倒塌开始就有人嚷嚷着“加缪说得对”,之后就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人们开着倒车说:“看看加缪《反抗者》里的鲨康内容——他可真右(right)啊!”加缪摇身一变成了法国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爱的大先知——萨特要是还活着就得说他们全是一帮猪鼻子插大葱的假知识分子。保罗·尼赞叫他们“体制的看门狗”。
加缪在右翼圈子里可以称的上是伟大复兴了。这时他还没那么火。大概是1994年,出版商小心翼翼地出版了《第一个人》,那本在加缪车祸现场找到的手稿。发行量很小:5000本、简装、不是标准版本,只是加缪读本中的一部分。结果一出版就卖疯了,加印立马安排上。人人都喜欢,加缪热突然就开始了,因为加缪大家展示了一个理想化版本的殖民主义。
加缪谈到作为受害者的定居者。酿酒师为了不给阿拉伯人用把葡萄树全都毁了。说来讽刺,这些葡萄树是法国人把橄榄树连根拔起之后种的,这样他们就能在穆斯林的土地上酿酒。加缪《第一个人》是对历史的完全重写,它虚构了欧洲人是非洲的、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土著这一点,结果大获成功。法国知识界和法国舆论乐见加缪殖民者故事里主人公的幸福故事。从此以后,加缪的书和关于加缪的书接连出版。
加缪热让法国出版社赚了个盆满钵满,尤其是出版社里名气最大的伽利玛。有漫画书,还有数也数不完的加缪传记,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出版社出的。它们一般有两到三部加缪传记,对加缪文本的解释,甚至还有写真集——他到哪都拍照——这个那个一大堆。电视上的纪录片、他女儿的采访,什么都有。我认为,加缪热真正兴起是在苏联陨落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过他的第一部小说对法国殖民主义的重估。
法国当代知识生活中对国家支持的普遍主义神话正在擦除殖民主义的真相,让加缪为此站台是再好不过了。读完他的所有小说之后肯定会觉得,“法国殖民主义也没那么坏嘛,哪里没有好人坏人”。他是今日新殖民主义世界的作者,而新殖民主义想要以一种乡愁般的态度回望殖民地的过去。
难道这不是对殖民主义漫画般的再-创造(re-creation)吗?这种戏仿意味着在殖民主义历史中不存在任何罪恶。加缪就是各路出版商、政治家和学者的及时雨:他们不想让文学中存在任何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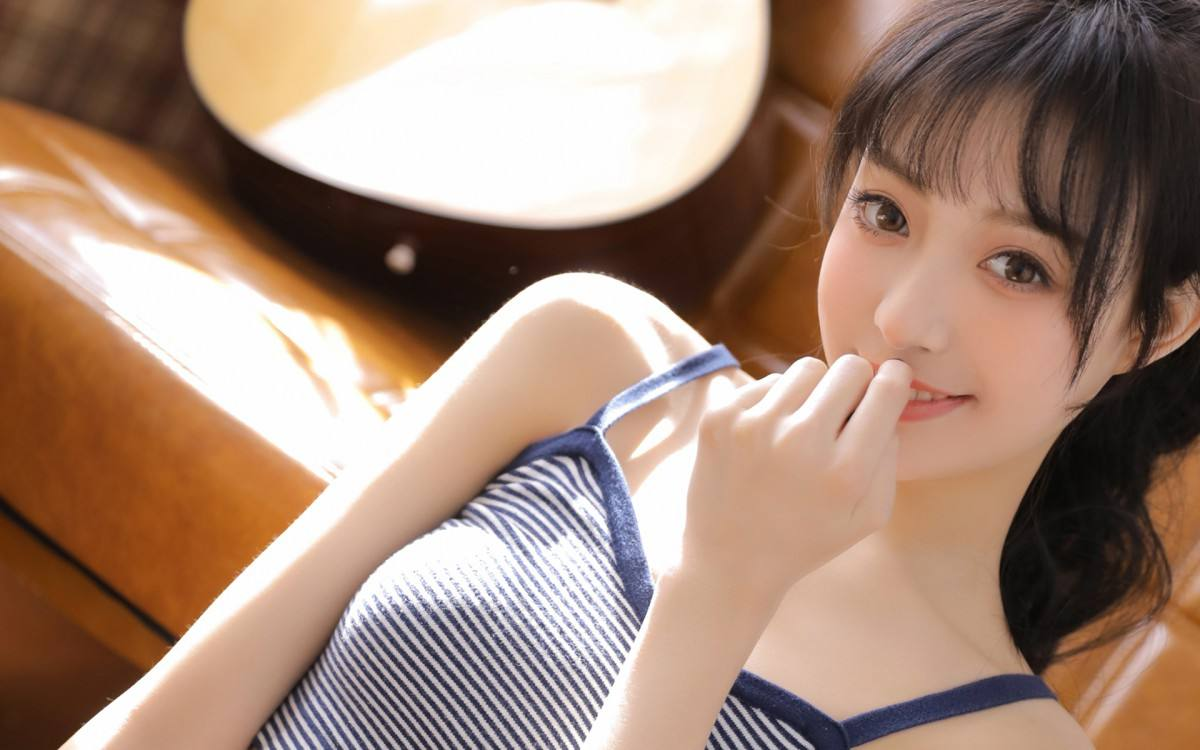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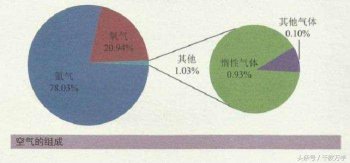

快来评论,快来抢沙发吧~